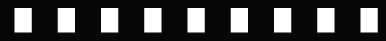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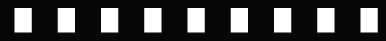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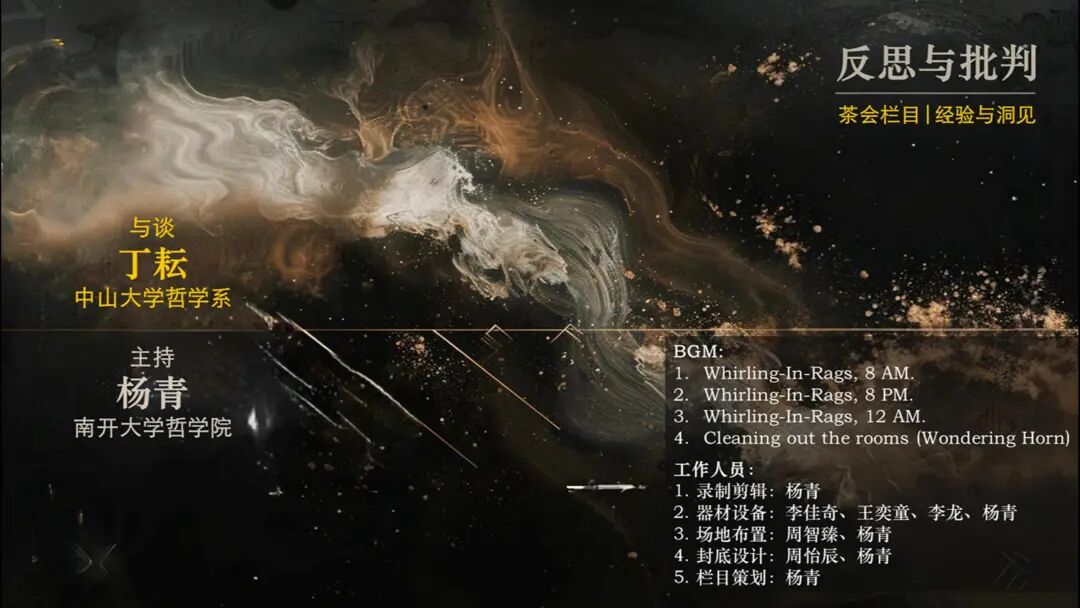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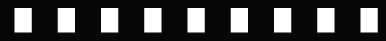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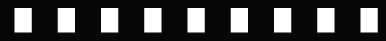
“反思与批判”系列上新“茶会栏目”!“茶会”是对本系列严肃内容的补充,旨在以速访形式为当期学者的哲学人生与自我理解生成快照、形成剖面,以期管窥这些在哲学领域带领我们前进的学者“如何研究、如何思考与如何生活”。
Introduction
杨青:各位学人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反思与批判“茶会栏目”。我是茶会主持人杨青。今天借反思与批判“中西马汇通”论坛的东风。栏目邀请到了丁耘教授,来成为我们本次“经验与洞见”茶会的主讲人,为我们介绍他的哲学历程和人生洞见。
01
杨青:丁老师晚上好。欢迎来到“反思与批判”茶会栏目。“反思与批判”系列一直有一个传统,是为我们每期的主讲人都依照讲座主题与其艺术旨趣设计一个“专题海报”。我们系列的美术设计师告诉我,在她拜托谢老师与您沟通时,您提到了自己“比较喜欢塞尚、马蒂斯和马奈”。我们非常好奇,这三位艺术家对您为什么如此特别呢?您的这一艺术旨趣与您的学术旨趣有什么联系吗?
丁耘:也不是说特别选择吧,之前没有人专门问过我特别喜欢什么画。正好这次谢老师为了设计海报询问,当时我就脱口而出了。我年轻时也很喜欢油画和雕塑。特别是马蒂斯,我是有机会看到原作,看到原作跟看复制品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塞尚是看到的画册,不过看到画册时我也特别喜欢。后来在16还是17年的时候,我在巴黎住过一段时间,在奥赛博物馆我看过很多次马奈和塞尚的画,在蓬皮杜艺术中心看过马蒂斯的画。
你问了之后我就反思了一下,就是为什么会特别喜欢他们,很可能是和他们都是后印象派的画家有关:马蒂斯更重,马奈、塞尚他们都是后印象派的画家。我刚做青年教师的时候讲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上课开玩笑说第一卷批判的心理学主义就是逻辑认识论上的印象主义。后印象派的画风很像现象学的追求,就是面向事情本身。到了很晚,我才发现梅洛·庞蒂专门写过一篇关于塞尚的很有名的文章。看样子现象学家喜欢塞尚是一个共同的趋向。就是怎样在“被给予性”当中,把事物本身结结实实的呈现出来。而马蒂斯的话,在我看来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西方的绘画,近代,或者说文艺复兴以后的绘画,特别是卡拉瓦乔以后,伦勃朗是范例,他特别强调光源。他画中所有的脸都是半明半暗的,光是从外面打下来。然后印象派包括后印象派有一个考验他们的特殊方法,就是看怎么处理阴影。看原作会看得非常清楚,阴影和阴影是不一样的,就跟中国画都是黑色墨,但分九种颜色。然后马蒂斯就不一样。光源就是有基督教背景的,光是从外面来的,从柏拉图到新柏拉图主义,讲光源都是上帝的光,是启示,你得栩栩如生的话,光就是从外面来的。但是马蒂斯所有绘画的颜色都是物体自己的,极其鲜艳,很惊人。就是他可能非常彻底的切断了物体本身与光源的关系,颜色是物体自己的美。
02
杨青:我们很多老师与同学都表示,他们是从丁老师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许多深入研究开始走近丁老师的。但与此同时也很想知道:丁老师最喜欢的中国古典文艺作品是什么呢?是什么契机让您与其结缘呢?
丁耘:我小时候的时候,我父亲的藏书比较多,他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他有很多的古书,我小时候文言文还看得比较多,什么都看。像是《古文观止》、《唐诗别裁》,最喜欢看明清笔记小说,就比如《聊斋志异》,我那时候看得很熟,初中就看了,感觉读起来很让人放松,也很简洁,表现力非常的强。到后面天热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什么消暑的设备,空调,风扇都没有,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夏天就读读庄子李商隐,很清热平静。听古琴也能有这个效果,能够让人去燥,有一种虚静的感觉——冬天不适合听,夏天非常适合。
03
杨青:我们通过一些公开资料得知,丁老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到复旦大学,从那里开启了自己的哲学研究历程。在这三四十年的研究历程中,您最怀念自己的哪一个时期,或者说,如果有一架不会产生“蝴蝶效应”的时间机器,让您可以回到自己过去人生中的某一段时间重新体验一遍,您最想回去哪一段时期呢?
丁耘:这个问题或者这一类的问题,我认为是不成立的,这是典型的史学幻想,就是假设你不是你。因为每一个人具体的自我和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缺了一环就是另外一个人,你不能假设有个可能世界里你父母不相遇,或者你父母相遇的时间不对,相遇时间不对,生出来的就是你的兄弟姐妹。这种问题的本质就是问一个人后悔不后悔。我从来不做这种假设。我刚讲座也提及,我是莱布尼茨派,现实世界就是最好的世界,没有什么可能世界。因为它在逻辑上不成立,这个问题的诡计就在这儿。
04
杨青:在2011年,您为复旦校庆106周年学术文化周致辞发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时为您的发言报道取题为“让哲学说中国话”。可以说,在我们国家强调“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今天,您14年前的这一发言相当具有前瞻性和洞见性。这次,您来到南开哲学参加的“反思与批判”系列也是我们的高端系列: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中西马汇通论坛。那么,我们的问题是:您认为要实现让“让哲学说中国话”,中、西、马哲学各自的任务、优势和困难是什么?
丁耘:这个话是2011年我所讲的。当时复旦的校领导比较重视文科,而且特别重视文科当中的青年教师。我当时也算青年教师,我们一些青年教师一起成立了思想史研究中心,影响也比较大。那时就跟干春松老师接触比较多,我不止一次请他参加思想史研究中心的年会。所以,校领导请当时还是副教授的我,一个年轻人做了这么一个发言。现在中山大学哲学系是特别明确的提出做中国哲学,像是陈少明老师,他们有一个传统,且非常的有自觉。这个做法我觉得非常好。实际上并不全是因为呼应了党的号召,党的号召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学术界也应该有个自觉的动力,像中山大学的老师在80年代就半自觉地走上了这条道路。我自己也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提过像“汉语现象学”的问题,像“走出翻译时代”的问题,我当时写过一些小文章,讲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我们不管学哲学的什么学科,你肯定是要先打好西学的基础。要整体地学习西方哲学,还不是只学一家一派,要整体地学,整体地学习之后你的视野就可以比较完整。但是,年轻人一开始读肯定是读译本,也不用自我欺骗。就像以前中国历代的大儒,包括一些高僧大德。读佛经肯定是读汉语的,能会梵文的有几个。然后佛教中国化的时候,这些译文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正像中国到了宋代就基本消化了来自佛学的刺激和挑战,于是它有一个自己的回应。这个回应不单纯是说简简单单说中国话。佛经附论也是中国话,虽然它有点翻译体,但它是依据中国传统典籍里的话去消化与回应佛家带来的思想刺激。比如说刚才讲到朱子,二程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但天理二字中,“理”字本来就有,《孟子》里就有提到过,但它是比较边缘性的,不是核心的。然后佛家,特别是华严宗是讲理事关系的。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在华严宗里面“理”就占据了一个特别中心的地位。然后就看怎么把佛家“理”的概念接过来。佛学中“理”就是空性的意思,儒家把它换了,换成伦理的内容,天理就是仁义礼智信,儒家用被佛家升格了的术语去概括三纲五常,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面对异质文明怎么开始讲中国话。我的探索中,虽然听起来很怪,为什么我会讲道体:朱子《近思录》第一篇就是道体,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部分就是道体。然后就是我们当代人,我们这一代,包括后面可能有更年轻的学者,努力用自己的母语去思考真正的哲学问题,而且这种思考是没有障碍的。我遇到过不止一个德国的、法国的哲学家问我:你拿中文来研究比如西方哲学的问题,有没有感到被殖民?我说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种语言,就是一个莱布尼茨式的单子,它是“一个”,但是它“包含了全世界”——单子就是这个意思,在内部映现着全世界。中文是非常美,而且最好的一个方面是非常有弹性的语言。它不是屈折语,屈折语是要变格变位的,词性要变,你学过外语就知道,这非常麻烦。但中文靠排列组合就能表达一切。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拿中文来思考哲学,不是中文的问题,是我们“这些人”的问题。
05
杨青:谢谢丁老师!也是在您的这一致辞发言中,您提到了马克斯·韦伯。可以说,很多中国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者都是以韦伯的《以学术为志业》作为学术生涯的自我反思的启蒙文章。在今天,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快速发展与文化工业的日益复杂庞大,一方面似乎带来了社会知识生产的新的增长点,一方面也似乎加剧了一直以来都存在的“文科无用论”。这不是当代青年学人面对的唯一问题,却也是一个典型问题:很多同学与青年学人正是在面对着这样分裂的社会反馈的情境下,继续在坚持从事哲学研究。我们想请问丁老师:您认为在当代继续“以哲学为志业”,有哪些不同于您当时的契机与优势?又有哪些特有问题呢?如果让您送给当代想要继续“以哲学为志业”的青年学人几句话,您会说什么?
丁耘:这个问题很实在,是这样的:马克思·韦伯有两篇“志业”文章,一篇是《以学术为志业》,另一篇是《以政治为志业》。志业是“Beruf”,不是单纯的职业,甚至不是单纯的立志。在新教伦理里面有一个被召唤的意思,受召唤。中文里“志”这个字主观能动性太强,实际上是有一个被天选,被强烈地召唤的意思。甚至你有点不情愿,但这就是天意,让你必须走这条路,没有其他选择。这是路德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的时候灌注的意思。你看韦伯一脸苦大仇深,是很沉重的,因为这不是好玩的事情。所以这并不是说单纯的兴趣,甚至要超过我们中国人说的志趣,比志趣的语气还要重一些。就是你觉得你逃也逃不掉的感觉,如果没有这种感觉,就别玩了,确实很沉重。天命也不是得意洋洋的——天命就是是天的意志,命是命令的意思——因为今天这条道路是很艰辛的,如果你没有强烈的像中文所讲的使命感——这种被召唤的,被应答的感觉,即你是在召唤面前“被应答”的这种感觉——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感觉,这条路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人工智能的问题。实际上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还在迅猛地发展,它想成为“代理”。我们讲“Agent”是主体,也有翻译成智能体的,其实就是“代理”的意思。代理就是说你把很多你不必亲自做的事情让这个工具去做。但要搞清楚这一点:你是不是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被代理。开玩笑说,您还亲自吃饭吗?您还亲自饮食男女吗?有一些事情是不能让步的,就是“生活”,是不可能被让步的。哲学一开始起源于什么?苏格拉底说——虽然听起来像心灵鸡汤,但是完全正确的——不经过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真正的生活就是要经过哲学反思。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哲学是不可能让渡给任何其他工具,否则你的活着跟植物人的活着有什么区别?比如说科幻电影《黑客帝国》里面,它实际上有一个苏醒的过程,那就是它那个形态的哲学的过程——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迫切需求,是为了自由,为了不被欺骗的迫切过程。所以真正的哲学是不可能被 AI 替代的。关键在于你要学会怎么用它。简单说来,教练员可能打得不比运动员好,但却都是教练员在排兵布阵。大语言模型能有多么精彩的回答,是取决于你怎么问它问题。你问得越精彩,它回答得就越精彩。总而言之,组织问题的能力是你自己的,现在不读书研究思考的话,未来怎么可能问它好的问题?
杨青:谢谢丁老师。《庄子·外物》中为我们讲过一个“得鱼忘筌”的典故,韦伯、批判理论和罗尔斯等都分析过类似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和“合理性”等等概念。这些典故和概念都重述了一种以整全的、属人的思考对抗“技术异化”的警醒态度。
将这一思考置于哲学学习之中,可以说丁老师今天的分享和传讲为我们补上了这一课,为我们思考个人的人生选择、哲学学科、社会历史的等等的发展方向和经验趋势给足了提醒和鼓舞。再次感谢丁老师。
End
杨青:那么,各位朋友,我们本次的“经验与洞见”茶会就到此结束。期待丁老师下次光临南开哲学,为我们带来新的知识、新的学问、新的经验和新的洞见。
这里是南开大学哲学院。我们下次茶会,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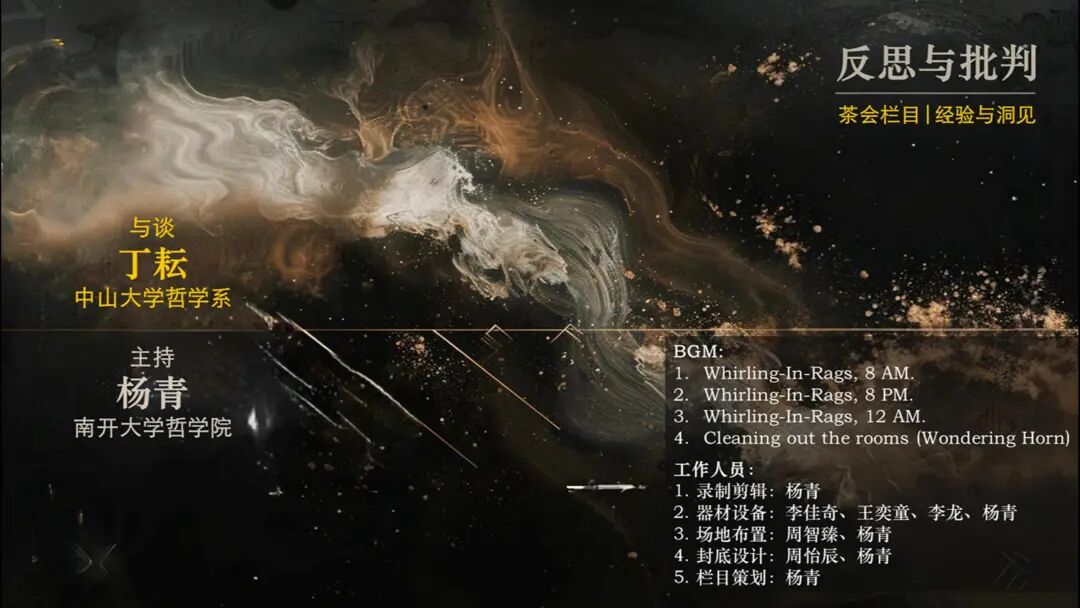
特别注意
B站反思与批判账号已有往期讲座录像,欢迎关注!

文案:罗海铨
排版:杨青
编辑:支阳
审核:谢永康




